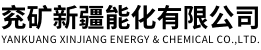我们村西头的老槐树下,总坐着几位老人。每当提起“勤廉”二字,他们总会说起我爷爷的故事,说那是“烙在黄土里的清白”。
爷爷是个老农民,一辈子没离开过土地,也只读过三年私塾。但他常说:“咱庄稼人,手上有泥,心里得干净。”
那年冬天,县里下来一个农业扶贫项目,要给村里发优质玉米种子。爷爷被推选为分发种子的负责人。消息传开,我家那间老屋顿时热闹起来。
邻居二牛叔第一个上门,拎着两瓶酒:“三爷,我家地多,您看那种子……”
爷爷把酒推回去:“该多少,是多少。酒拿回去,给你老爹暖身子。”
堂婶也来了,塞过来一兜鸡蛋:“大伯,您孙子正长身体呢……”
爷爷叹了口气:“孩子吃鸡蛋长身体,咱吃了这鸡蛋,脊梁骨就挺不直了。”
最让我难忘的是发种子的前一天晚上,村主任来了。他是我爷爷看着长大的,说话直接:“老叔,给您留了三袋最好的种子,今晚就拉您家院里。”
爷爷正在磨镰刀,头也没抬:“为啥?”
“您辛苦一辈子,该得点好处的。”
爷爷终于抬头,眼睛在煤油灯下亮得吓人:“这种子是让庄稼人吃饱饭的,不是让谁得好处的。”
第二天分发种子,爷爷第一个打开村主任说要留给他的那三袋,当众抓了一把:“这种子最好,谁家地最薄,谁家先拿!”
事情本该到此为止。谁知秋收时,用了那批种子的人家都大丰收。村民自发凑钱,要给爷爷“表示表示”。
那天傍晚,村民们聚到我家院里,桌上放着一台崭新的收音机——爷爷最爱听戏,他那台老收音机已经杂音很大了。
爷爷从地里回来,满腿是泥。他看看收音机,看看乡亲们,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他走到墙角,提起三袋早就准备好的东西——那是他用最好的玉米磨成的玉米面,每袋足足五十斤。
“心意我领了。”爷爷声音沙哑,“但东西不能要。这三袋面,是我自家地里长的,你们拿回去尝尝。种子是好是坏,尝过才知道。”
村民们愣住了。爷爷接着说:“咱庄稼人不讲大道理,就认一个理——地不会骗人。你流多少汗,它就结多少果。这种子是国家给的,功劳是国家的。我要是收了你们的礼,就是偷了国家的功劳,这跟偷庄稼有啥两样?”
那一刻,夕阳西下,爷爷站在那儿,身后是金灿灿的玉米垛,整个人像地里的一棵老庄稼,根扎得深深的。
最终,收音机被退回去了,三袋玉米面却被硬塞给了村里最困难的几户人家。
很多年过去了,爷爷已经离世。但每年玉米丰收时,村里人还会说起“三袋玉米”的故事。父亲接过爷爷的担子,成了村里各种项目的监督员,从未拿过一分不该拿的钱。
如今我在城里工作,每次面对诱惑时,总会想起那个黄昏:一个老农民,用三袋金黄的玉米,教会了我什么是廉洁——它不是高悬的匾额,而是长在地里的庄稼;不是响亮的口号,是磨成面粉后依然留香的实在。
这份来自土地的家风,比任何财富都更珍贵。它让我走在任何路上,都能脚底沾泥,心中有底。